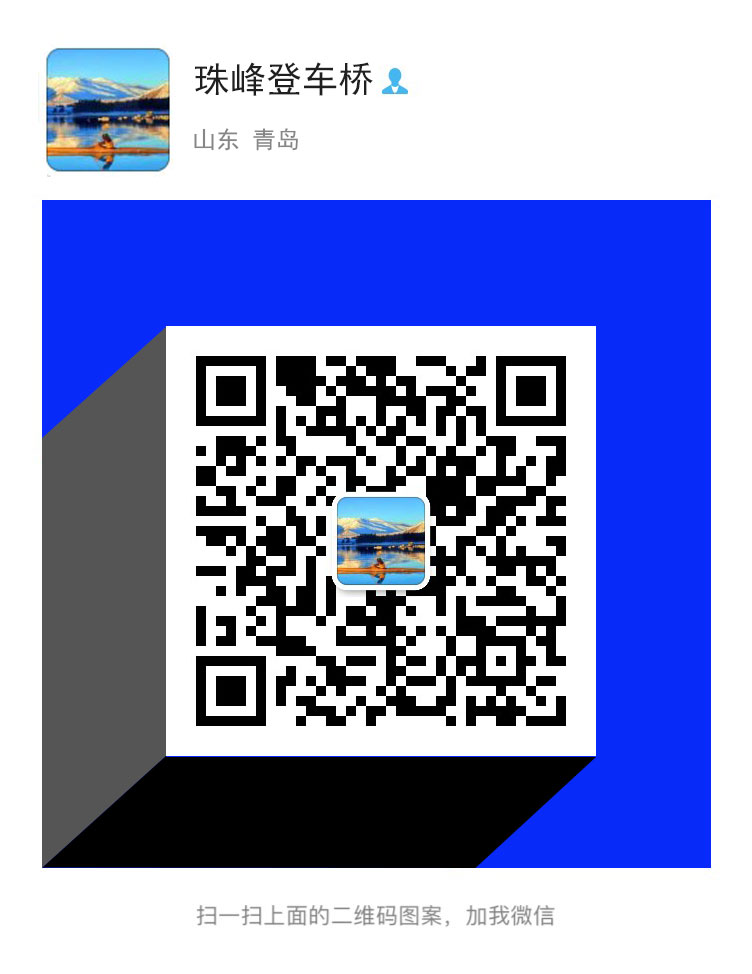新质生产力要让工程师文化重新变为时尚-潘禺
随着全国两会的召开,“新质生产力”慢慢的变成了了引起中国各界人士讨论的互联网热词。
这个基于快速变化的现实问题被提出的重要概念,意在摆脱传统经济稳步的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以科学技术创新为主,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
中国社会的变化非常迅速,新中国经历了70年经济总量超过170倍的增长,人均寿命增加了40多岁。对中国人来说,“新”这个字不仅是蓝图的擘画,更是对现实世界的直观感受和唯物主义描述。
在中国,2020和2000就已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这短短的20年里,GDP增加了10倍以上,高校毕业生也增加了10倍。20年里结构性的差异也很巨大,2023年,接近70%的适龄人口可成为本专科大学生,而在二十年前的2003年,这一个数字还不到20%。
在这快速变化的20年中,城镇化率接近翻倍,出生人口则接近腰斩,每个新生儿得到的不仅是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生活水平提升,还有人均教育资源的显著改善。
这20年也是数字技术在中国快速地发展的时期,新一代成长起来的数字时代的原住民们,他们所希望从事的劳动和所追求的美好生活,将在若干年后与过去的社会结构、生产力水平不相匹配。每年超过1000万的高校毕业生所要求的高质量就业,必须以社会结构的变革来适应。
中国的城镇化率在2010年就已突破了50%,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若干年后的大学生中有一半以上的生活成长环境是在城市,也代表着多数高校毕业生对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有更高的底线年年末人口数及其构成,其中城镇人口已达66.2%(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研究中国创新型企业的封凯栋教授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他在2020年对全期120位同学做了一个调查,只有20人有机会、并且愿意从事机械工程相关行业,其他大部分都转行了。
这意味着,在大量的传统岗位不足以满足中国大学生的就业需求时,就需要新的就业场景。而以创新为主导的新质生产力,能够完全满足这种期待:提供更多体面舒适工作,让千千万万大学生更有自由和闲暇的生产力。在我的理解中,新质生产力的目标是推动慢慢的变多这样的岗位出现:操纵无人机的快递配送员、端着平板电脑编写小程序的车间工人、自动卸货设备的遥控者、在AI辅助下一个次品都不错过的质检员。
新质生产力的目标也是推动数字与低碳技术对工业和生活场景的全面赋能,太阳能电池收集的绿色电力被越来越廉价地有效储存起来,用于饲养中国人爱吃的海鲜水产或者给电动车充电,慢慢的变多的自动化与无人值守场景出现在工厂、矿山、港口和仓库。
洋山深水港无人码头超远程指挥中心,实现对百公里外的集装箱的精准抓取与码放(图片来自:新华社视频截图)

新质生产力的目标更是通过工业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算力的运用,让每个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真正变成“劳心”而非“劳力”者,劳动的主要过程越来越集中到开始的协商、规划,事后的维护、验收,而中间过程,特别是最底层的“脏活”场景,被大规模标准化、智能化自动解决。
这样做会消灭大量就业岗位吗?答案是会,但也会有更多更高价值的新岗位涌现出来。例如,从运货的马车夫,到运货的卡车司机,再到远程调度智行货车的调度员,体验虽然在升级,岗位总数并不会大量减少,因为调度员虽然消灭了好多个司机岗位,但增务支持这位调度员的大量工程师。上述这些场景绝非只是想象,而是已发生的现实。例如,工业版人形机器人Walker S已开始在蔚来新能源汽车工厂“打工”,参与了门锁质检、车灯盖板检测、安全带检测、贴车标等工作。
优必选工业版人形机器人Walker S已经在新能源汽车工厂“实训”(图片来自:深圳特区报)

这背后是中国确实已发生了产业体系的转变。从外贸上看,已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增长的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这个出口“新三样”,去年已经突破了万亿,在逐渐取代服装、家具、家电这个出口“老三样”。像电动车这样的产品由于设计和生产的智能化,可以带动大量软件工程师、AI算法工程师、机器人工程师等岗位。中国有这样的机会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创造新就业。作为反例,对于去工业化、基建更新陷入基本停滞的国家来说,上述的场景就难以发生。纽约的第一条地铁于1904年建成,当时的中国还在大清朝。如今的纽约地铁还是这套系统,员工手动记录列车的运行,用手柄操作陈旧的信号灯,1970年代的R46列车还没被完全替换。纽约有13%的地铁乘客逃票,45%的公交乘客逃票,对此居然没有一点智能化的解决方案。
为什么传统的机械工程、土木工程岗位不能留住青年才俊,而上述这些新岗位可以?这就要说到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为什么需要被重新估值,怎么样才可以重新估值。
关于估值与分配,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至今尚没有被理论超越的经典,只不过需要与时俱进。生产力的三要素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手段)、劳动对象。经济现象表明,从劳动手段来看,非实体性的科学技术、知识产权等占据主要价值,从劳动对象来看,不被经典理论认可的非物质生产占据主要价值,这样的生产力慢慢的被价值高估。譬如一家软件公司,其开发的产品是虚拟的(可以有物质载体比如光盘拷贝,也可以只有数字版本),但毛利率往往明显高于一家开发硬件实体(譬如汽车)的公司,能支付给员工的薪酬也更高,劳动者的体验也更接近“白领”。
电动车虽然是“先进”的,但利润的大头也并不在实体的车上,而往往在某种虚拟的服务上,如智能驾驶。所以综合看来,为什么微软的毛利率远高于特斯拉,金山办公的毛利率远高于比亚迪,尽管这都是中美各自行业的头部代表公司?背后的原因也是如此。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相比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等,金融、计算机、软件工程这些专业更受到大学生青睐。莫说拉动土木工程、机械工程就业的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已经陷入困境,房地产供需关系已发生重大转变,就算房地产下行周期没有到来,愿意“进厂”的大学生也是越来越少。
不仅大学生如此,当城镇化率进一步走高,农民工的第二代也很难出现在建筑施工工地。研究城市规划的赵燕菁教授在谈到地方借债建设基础设施时就说:“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建,下一代人根本不会干这活了。你想想,让你的小孩到工地上去,干现在农民工干的事,会干吗?脏活一定要在我们这一代给干了。”
2024年2月29日,2024CME国际机床展于上海举办,图为国产中星数字控制机床(图片来自:IC photo)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提到,由于中国政府的约束造成场景壁垒,中国不会在医疗、法律等高端服务业场景中,创造美国那样高估的GDP,最近韩国医闹事件也是说明医疗GDP与政府约束高度相关的案例。由于许多公共服务场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约束了其价值的高估,中国经济依然需要制造业的升级空间,需要实业作为强国的中流砥柱,不能发生美国那样剧烈的脱实向虚,何况美国以高达83%的城镇化率,依然努力试图让制造业回流以满足铁锈地带的选民。
因此,在继续扩大服务业以满足新一代年轻人的同时,就必须实际做到对工程技术人员的价值重估,让工程师文化乃至工人文化重新变得时尚,对城镇受教育人群更具吸引力,只有这样才可以继续保持完整全面的工业体系和自主可控的供应链。分配改革要在不同的方向长时间坚持,不仅体现在需求侧的保障,也就是财税政策和转移支付等二次分配中,也体现在新质生产力代表的供给侧改革中。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传统的三个产业的边界将被渐渐打破,和工程技术人员一样,农民的工作也会更多接入数字技术。总的趋势是,劳动手段越来越依赖非物质工具的科技与知识,而劳动对象则混合了物质资料与非物质资料,以非物质的数字技术来解决物质世界的任务。
实现了温湿度、光照、二氧化碳浓度、空气循环等全自动化控制(图片来自:IC photo)

由于数字技术的赋能提升了单位劳动时间的价值创造,也优化了劳动体验,新的业态会涌现出来。大量的高校毕业生已经在运用网络技术打破8小时集中办公的工作传统,如直播电商、自媒体创作、远程兼职服务等,人们对“灵活就业”的观念和认识迟早会改变。我们已看到新技术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也吸引走了一部分劳动力,所以经常会有“满大街外卖员是不是浪费劳动力”“年轻人为啥不愿意进厂了”“宇宙的尽头是直播带货吗”这样的疑问,而这正是新技术给我们提出的新问题,也是发展阶段的问题。在AI更多渗透到工作生活中之后,工作和服务场景都会趋于标准化,难以也没必要再通过内卷式恶性竞争来占领市场,工程技术人员也会有更多时间进行闲暇娱乐和消费,这既是工业与服务业的融合,也是相互促进。
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历时多年的科教兴国与大学扩招就非但不是带来沉重的负担,而是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技术的研发是需要堆人的。苹果汽车研发投入2000名工程师,最终放弃。对比来看,比亚迪研发智驾就有4000人,华为研发智驾就有7000人。蔚来有9000人的开发团队,宁德时代有18000人,只有中国能够支撑这样的工程师规模,也只有中国能产生这样的工程师文化与教育环境。
中国普及穿透社会各个阶层的教育与通信基础设施,使得一个规模巨大、熟悉信息技术的年轻知识人群成为可能,在这个基础上,让他们的工作都能走向安全、智能和高端,将创造一轮设备与服务升级的大规模有效需求。
那些愿意符合新质生产力的资本和企业将能够抓住这一个市场。不追求过度的资本回报,而将更多的收益投入到研发技术,投入到工程技术人员的待遇提高、劳动福利改善、劳动手段升级中,这样的资本和企业会在未来得到大发展。而不这样做,继续旧的利润分配模式,甚至还在以延长劳动时间、内卷式恶性竞争作为手段的资本和企业会被逐渐淘汰出清。
这一过程并非完全由政策主导,新质生产力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概念,过去这些资本可以用旧模式生存,是因为“新时代”还没到来。但还是那句话,形势永远比人强,走向2030的中国许多基本国情和客观条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已经比任何人为的改革推动力都更紧迫。站在这样的战略关口,能不能用新质生产力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对好工作的向往,已经时不我待。